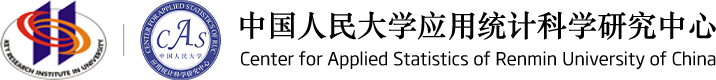1950年代产值问题讨论回顾(四)——算法要不要改,王思华这样说
2022-03-16
工业总产值的计算方法要不要改
总产值的种种问题都是大家承认的,但如何看待、解决这些问题,则有很大争议。相关讨论多数集中于工业总产值存在重复计算这一问题,改还是不改以及怎么改,出现了不同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彻底改进工业总产值的计算方法,将“工厂法”所谓在企业范围内不允许重复计算的规定依次扩大到“托拉斯”、工业内部的部门、整个工业部门,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即采用托拉斯法、工业部门法、国民经济法计算工业总产值,在对应范围内消除重复计算,以此计算各个范围内的“最终产品价值”。
“本刊编辑部”在其综述性刊文“在工业总产值计算方法中需要讨论的几个问题”中转述了这种观点的基本思路。“工业总产值指标可以根据其目的的不同,分别采取以下各种方法:观察工业企业内部各个车间的工业总产值,可以采用总周转额指标,亦即扣除车间内部的各种重复因素,但不扣除车间与车间之间的各种重复因素;计算工业企业总产值时,可以采用工厂计算法;研究行业内部各个工业部门之间的此例关系变化情况时,应該采用工业部门法,亦即扣除各工业部门内部的各种重复因素;研究工业与农业的比例关系变化情况时,应该采用工业法,亦即扣除工业内部的各种重复因素。这样,既符合了工业总产值应该包括C +V + m的理论依据,也可据以正确地计算工业与农业以及工业内部各个部门间的比例关系的变化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同期《统计工作》还刊载了“本刊编辑部”另一篇综述“关于工业总产值计算方法的资料”,其中明确说“苏联在计算工业总产值时除按工厂法计算外,尚有托拉斯法、部门法、整个工业法、国民经济法”,还分段对这些方法做了简要说明。鉴于当时的背景,不难想象,国内之所以能够提出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就是受苏联经验影响所致。
显然这是一个比较激进的解决方案,有很多文章不同意做这样的处理,认为其不切实际。与此对应的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维护现有做法,另一种则认为可以针对农产品初加工做一些改进处理。岳巍在“关于工农业总产值统计分类和计算方法的几个问题”中曾经对“工厂法”工业总产值的合理性做理论论证,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王思华所撰写的“关于工业总产值的商榷”,此文结合实际应用,对工业总产值的方方面面做了比较全面的讨论(此文刊出之前,“意见的分歧在哪里——关于工业总产值计算方法问题的讨论”一文曾经较为详细地转述了这些观点)。以下主要引用王思华文章中的观点,显示对各种处理方法利弊的思考,以及对种种质疑的回应。
王思华对此有系统论述
总体而言,王思华通过此文表达了三层观点。
第一层,开篇提出并回答:“为什么我们要采用“工厂计算法”来计算工业总产值呢?因为工业企业是社会分工的基层环节。我国目前的生产管理系统是以企业作为基层单位的。企业是社会上的一个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因此,只有“工厂计算法”计算的企业总产值,才能和当前的工业管理工作相一致”。“我们必须在各工业企业最后完成生产过程时计算其产品的全部价值,这样才能表现企业的产量情况”。就是说,以工厂法计算工业总产值,是以企业为基层单位的管理系统的内在要求。如果管理体系不改变,工厂法就不能抛弃。这显然是一个大前提。
但是,王思华的论证仅到此为止,没有继续讨论为什么一定要以工业总产值作为管理指标,这样应用给企业管理会带来的问题,以及有无可能找到替代指标,只在结尾处简单回应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对工业总产值的滥用问题,认为“这些情况的产生,不能归咎于总产值这个指标本身,而是在于企业管理方面如何运用总产值这个指标的问题”,比如“只注意检查总产值的完成情况,忽视了品种计划和质量计划完成情况的检查”,“这是片面的做法,应该纠正”,但如何纠正则没有展开。也就是说,王思华此文主要集中于上面我们提到的工业总产值的第一个争议点,搁置了有关第二个争议点的讨论。后者则是孙冶方的“从总产值说起”一文的讨论重点(具体见本文后面的讨论)。
第二层,从国民经济层面针对工业总产值存在重复计算这一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简要总结相关争议之后,王思华明确表态:“如果我们要表现社会产品的周转额,要表现各企业之间的实际商品流通额;如果我们是从社会再生产的观点出发,要反映社会产品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之间的交换过程,或者为了反映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也就是分析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如何按价值和物质形式补偿的问题,或者是为了说明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在生产上的物质联系,那么,所谓社会总产品,就应该是各物质生产部门所生产的产品的总和。社会总产品中应该包括着各企业之间的产品周转额”。也就是说,在此前提下,工厂法工业总产值这所包含的各个企业之间的重复计算就是合理的。
文章承认,“社会产产品周转额应该不同于社会生产的最终产品总额,……后者是一定时期内社会最后所生产的有使用价值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它是社会总资本的产品,而不是个别资本的产品,因此,不应该包括重复计算”。所以,将工厂法扩展到整个工业法计算总产值的想法,“在理论上是可以说得通的”,但“在我国目前实际工作上,是否即采用这个计算方法或采用其他方法”,还需要进一步考虑。
文章迅速提出最具实质性的问题:“我们计算工业生产活动的成果,应该采用总产值,还是净产值”。他认为,对工厂法总产值的修改,“可以按照工业法或整个工业法计算总产值,另外也可以计算生产净值”,也计算净产值。对此王思华的回答是:“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要说明一定时期内的整个工业为全社会所提供的产品总量,是要确定全部工业企业最终所生产的产品总量,而不仅仅是新创造的产品价值时,那么在这个场合,便只有总产值这个指标才能确切说明问题”。因为“我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统计,既要按社会产品的物质形态来规定它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又要按其价值表现来规定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社会产品,当它表现为一定的价值量时,都是由两部分组成的:转移价值和新创造价值。转移价值代表着生产资料,是过去劳动的结果,是装备活劳动,提高其生产效率从而增加社会产品的有力的生产因素”。
文章认为,“任何经济指标,都有它的特殊目的性和局限性;如果想使一个经济指标都能很好地说明国民经济的各种复杂现象而不存在任何缺点,是不可能的”。总产值固然有问题,但净产值也有其局限性。文中这样归纳净产值存在的问题:“净产值受价格的影响较为突出,本部门所创造的净产值并不一定在本部门内实现,因此,用净产值来反映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也是不够正确的,例如砂糖工业由于利润高,它的净产值便大,硫酸工业的利润低,它的净产值便低”。
第三层,说明如何看待以及如何解决总产值在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用总产值表现工业与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另一个是不同工业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比较。
关于工业与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文章先对问题做描述,“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将以更多的原料供应工业,因此,工业总产值中所包括的农产品原料部分也会不断增加”。尽管同时“工业供给农业的机器、设备、用具、肥料等工业制品也会越来越多”,会产生一定的“削弱作用”,但鉴于“中国是一个广大的农业国,对农产品进行简单加工占了整个工业的很大比重,且中国工业企业单位多,規模小,一种产品往往须经过许多企业才能制成一个完整的产品,因此,在工业总产值中包括着很大一部分转移价值”。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文章先后提到两个方向的解决办法。一个与计算方法改进有关:“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特点,对农产品进行初步的加工,如其工序是局部的简单的,例如轧花、木材加工、手工屠宰、手工碾米、手工磨粉、缝纫等都可以当作工业性作业来处理。即只计算其加工价值,而不计算其全部产值,这对于防止夸大中国工业总产值的情况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另一个是指标应用上的选择:“全部工业中包括着小工业和手工业,而小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的程度”,所以,“为了更确切地说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程度”,“用全部工业与全部农业进行对比”不够科学,“采用大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这样的指标,更有其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意义。因为我国进行的工业化,不是发展一般工业,而主要是发展大工业:大工业才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有关劳动生产率的比较问题。文章转述由于转移价值大小不同给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比较带来的问题,“1955年燃料采掘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工人的平均产值是 4,119元,食品工业部门每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27,295元,后者的劳动生产率大于前者六倍,这 里显然是有问题的”。但作者认为,“在各个不同的工业总产值中,原料价值所占的比重不同,自然就使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发生很大的差异,这是由于各部门具有不同的组织构成的缘故”。作者由此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不同的工业部门,以价格所表现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只限于用总产值所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可能进行对比的”。“采煤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工人,远远超过于电力工业部门,那么,电力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起采煤工业部门就显得很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说前者的劳动生产率如何低于后者”。正确的对比方法是:“我们只有从各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上,从动态上来研究不同工业部门间的劳动生产率才有意义”。这明显地是没有提出较好的解决方法,为此文章还专门强调,“如果只是从静态上来观察不同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即使我们采用净产值这个指标,同样地也会表现出不合理的现象”。
一点评论
总体而言,王思华在文章中有关工业总产值的讨论,主要是“反应-应对”式的。一方面承认当前用工厂法计算工业总产值存在问题,同时论证即使采用净产值也同样会出现问题。针对总产值在应用上的问题,比如工农业比例关系的计算,提出了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但在如何对待劳动生产率各部门间不可比问题上,则显得有些牵强。此外,有关工农业增长速度上存在的问题则基本上忽略,没有讨论。
进一步看,王思华在文中涉及到一些提法,对于今天的产值核算及其应用都有意义。比如,“净产值受价格的影响较为突出,本部门所创造的净产值并不一定在本部门内实现,因此,用净产值来反映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也是不够正确的”。今天我们用增加值计算产业结构,同样要面对因为上下游产品比价关系及其变化带来的影响——如果动力煤炭供应价格发生变化,就会直接影响煤炭行业和电力行业各自的增加值,从而影响这些行业之间的比例。又如,“为了更确切地说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程度”,应该“采用大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这样的指标,更有其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意义”。时至今日,为了前瞻性地反映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我们也不能简单、笼统地采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比等指标,而是要提炼一些主题,形成更具表现力的产业概念,比如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等,以这些产业占比作为衡量指标进行观察和分析。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大规划项目“中国统计学史”(项目号19XNLG01)支持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关于作者
高敏雪
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统计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统计学会副会长,是国家统计专家委员会成员、国家气候变化第三届专家委员会成员。研究领域以国民经济核算为中心,延伸到环境经济核算,并扩展到整个政府统计。
编辑 | 李金奇